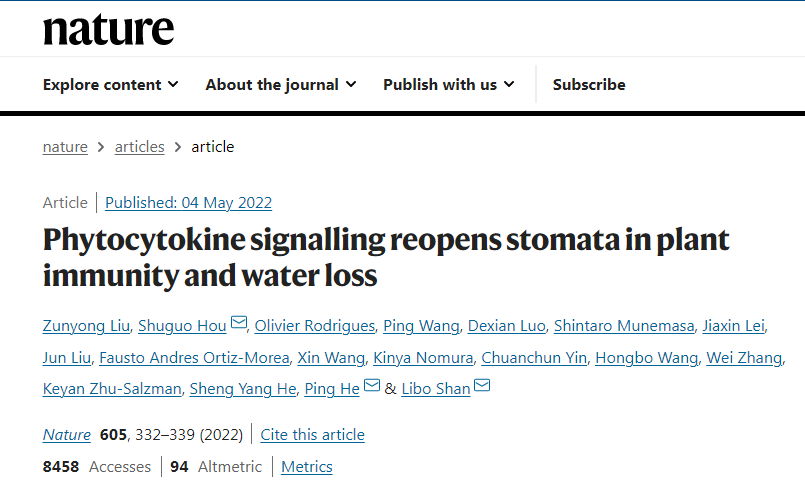
在《自然》上以共同第一作者兼共同通訊作者發表論文后,侯書國一時間成了學校的“紅人”。因為這是山東建筑大學自1956年成立以來發表的第一篇《自然》論文。
工作群里,不斷有人把相關的新聞鏈接丟進來,“重磅”“零的突破”“打破校史”……吸引眼球的詞匯一遍遍刷屏。緊隨其后的,是一排排點贊的“大拇指”。
侯書國的心情,卻從最初的喜悅,逐漸變得“忐忑不安”。
在山東建筑大學市政與環境工程學院里,侯書國所從事的生物工程研究并非優勢學科。但作為42歲的副教授,在這個學校就職15年后,他終于在頂刊發表了論文。
然而,面對《中國科學報》的專訪,侯書國沒有表現出太多“逆襲”的快意。
“因為成果是屬于過去的。”而對未來,他還不是那么有把握。
從《自然》啟程,再抵達《自然》
侯書國等人的發現,揭開了植物中一對新“搭檔”的故事。
當病原菌入侵植物時,植物細胞會分泌名為SCREW的植物細胞因子,這種小肽類物質被細胞表面的受體NUT識別后,就會觸發一系列免疫反應 。
這項研究的一大亮點,在于揭示了“氣孔”在這個免疫過程中的作用。
遍布植物表皮的氣孔,是水分與氣體的交換通道,也是病原菌的“方便之門”。
2019年,還是《自然》雜志上,一篇論文講述了病原菌從氣孔進入植物體內后,如何促使植物細胞間產生更多水分,為自己創造適于繁衍的環境。
而侯書國等人的這項研究,從植物的角度,補上了雙方博弈的另一塊拼圖:植物沒有坐以待斃,它們會通過細胞因子釋放和受體識別這個過程,把氣孔打開,讓細胞間的水分迅速蒸發出去,從而抑制病原菌生長。
“令人興奮。”“這項工作非常有趣,拓寬了已知植物細胞因子及其功能的組合。”在評審意見中,審稿人們這樣寫道。
對大多數科研人而言,在《自然》《科學》這樣的頂刊上發表論文,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;以侯書國的背景和經歷,這件事則更難。

侯書國
侯書國的本科和碩士都就讀于東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,他喜歡在圖書館里翻閱各大學術期刊。某期《自然》雜志上,兩位植物免疫學的頂尖學者撰寫的綜述,把他“錘”進了這個研究領域。
“那是2003年。從那時起,我就對這個研究領域非常、非常感興趣。”
2006年碩士畢業后,他進入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,以技術員的身份繼續開展植物免疫研究。在這片著名的科技制改革“試驗田”上,他最初體會到了科研的無盡樂趣和滿足感。
然而,面對偌大一個陌生的北京城、無處不在的孤獨和壓力、已知和未知的憂慮,這個20多歲的年輕人沒能積聚起足夠的信心。
他最終選擇了放棄,回到山東老家。
剛好山東建筑大學新成立了生物工程專業,亟需相關背景的年輕人,他留了下來。因為當時只有碩士學歷,侯書國只能從助理實驗師做起,主要工作是為本科生準備實驗室。
但科學探索的樂趣,不曾嘗過也就罷了,食過髓知過味的人,總是難以舍棄。在這個沒有科研任務的崗位上,侯書國仍然堅持以前的習慣,每天清晨來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,就是查閱最新的文獻。
2012年,符合在職讀博條件的第一年,侯書國迫不及待地申請到山東大學在職讀博。在這期間,他發現了多種不為人知的、由植物分泌的小肽類物質,他推測這些物質可能參與了植物免疫調控。后來,才有中國學者正式提出“植物細胞因子(Phytocytokine)”這個概念,這個領域也逐漸變得熱門起來。
侯書國提前一年博士畢業,研究成果還被評為當年山東大學的“優秀學術成果一等獎”。
“經過一番天人交戰,我還是回來了”
在2014年,侯書國迎來了科研生涯的一次重要轉機。這一年他34歲,趕在“男性35周歲”的年齡紅線前,申請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青年科學基金。
一名來自“建筑大學”“工科學院”的“實驗師”,申請一個“植物抗病、植物免疫”的課題,乍看之下實在有些不搭調,但所幸成功了。
當年侯書國寫在申請書上的研究設想,正是醞釀出如今這篇《自然》論文的idea。他想,或許就是這個點子打動了評審專家吧。
“沒有這筆基金,我后面的一系列機遇都無從談起,也沒法完成后續的研究。”
2017年2月,在國家留學基金委和山東建筑大學共同資助下,侯書國前往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系,在何平、單立波這對夫妻教授的實驗室里做訪問學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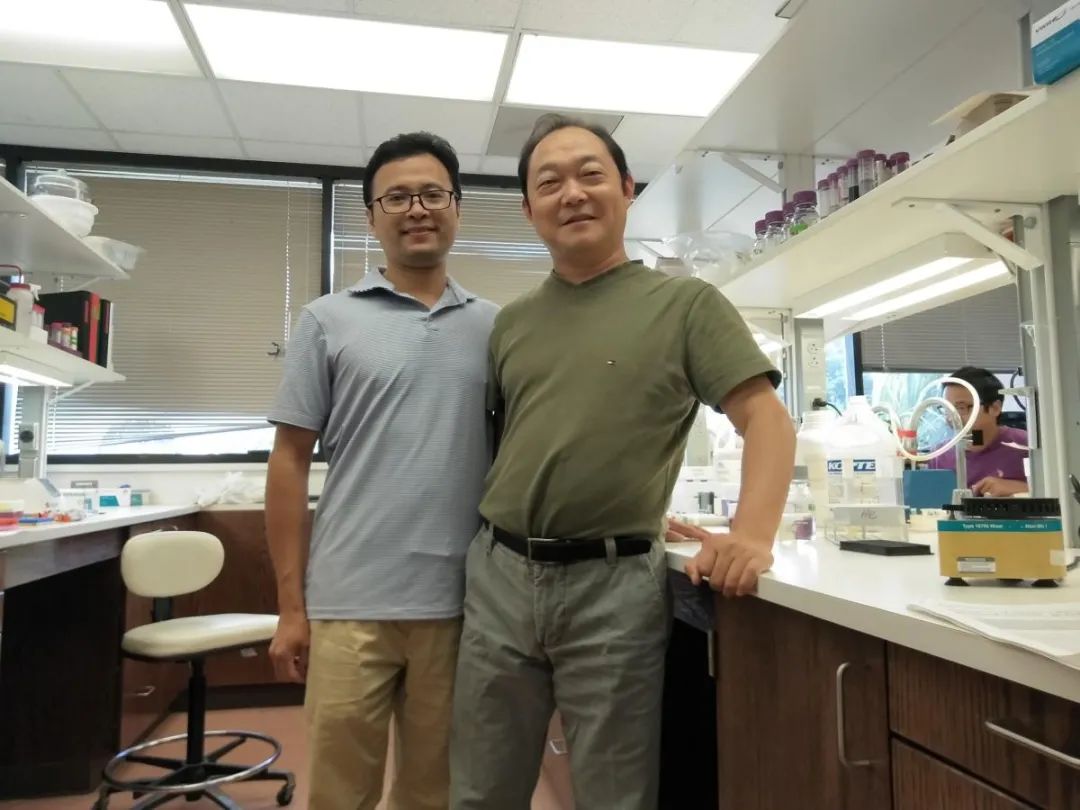
侯書國與何平教授合影留念
這期間,在兩位導師的指導下,侯書國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。他在這里的一系列科學發現,正是2022年這篇《自然》論文的基石。
約定的回國期限很快就到了,而研究還遠未達到發表程度。山東建筑大學的領導在了解到侯書國的研究需要后,同意為他延期幾個月。
“那時候,我非常希望能留在德州農工大學繼續做博后。但是我申請的這種訪問項目有規定:項目結束必須回國,至少在國內做3年以上的工作。”侯書國打聽到,身邊也有人違反規定堅持留下來,但這種做法對學校乃至國家都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響。“經過一番天人交戰,我還是回來了。”
回來后,科研平臺落差很大。好在第二年,趕上學院實驗中心儀器采購,侯書國借這個機會買了價值幾十萬的儀器,有了初步的科研條件。
但最“卡脖子”的是,當時他作為一名高級實驗師,無法組建自己的科研團隊。
管理實驗室之余,侯書國會為自己收拾出一方小小的實驗區,堅持開展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。很多時候,哪怕是一瓶試劑,也要自己親手配制;哪怕一個簡單的實驗方法,也要從頭開始摸索。
而他無法繼續開展的那部分工作,主要由德州農工大學的一名中國博士后劉尊勇接手。他與合作者們一直保持著密切的線上聯系,通過視頻的方式討論實驗進展。
論文在《自然》上線那幾天,學校受疫情影響,還處于封閉狀態。校領導和學院領導通過微信聯系侯書國,表示愿意支持他建立研究平臺。
“成果屬于過去”
“成果屬于過去”——對所有科學家都是如此。但對侯書國來說,這句話更顯沉重。
“因為這個‘過去’,終究是依靠別人完成的,其實我一直很想證明,只靠我自己,能做到什么樣。”
他想知道:自己有沒有能力領導一個團隊?能不能跟上領域發展的步伐?能不能再度做出前沿創新的成果?
但面對未來,不確定的因素實在太多太多。
23萬元的青年科學基金,支撐他從2015年走到了2018年。2019年,他再次申請面上項目時,卻失敗了。
2021年,當他的論文在《自然—通訊》上發表時,很多人鼓勵他,說這次肯定沒問題了。但他躊躇良久,硬是沒敢申請。
“如果連續兩年申請不中,今年就要停止申請一年,我不敢冒險。既然現在《自然》上的論文已經發表了,我決定再試一次。”
那么,下一步準備怎么克服目前的種種局限,繼續開展有價值的科研工作呢?
聽到這個問題后,侯書國停頓了幾秒,然后緩慢地說:“這是您所有問題里,我最難回答的一個。”
讓他卡殼的,除了科學本身的問題,更多是科學以外的思慮:能不能申請到新的基金?在當前的疫情和國際形勢下,怎么找到合適的合作伙伴?如何建設一支有活力的研究隊伍?
對侯書國來說,他很遺憾沒能在40歲以前發表這樣有分量的論文。因為40歲以前,他還有機會去申請山東省內的一些青年人才稱號。現在,他超齡了。而那些與他年齡匹配的稱號,需要更高的競爭力。“至少在很多地方院校,對這些人才稱號要比論文更加看重。”
“我的起點太低了,盡管一直馬不停蹄地走啊走,但還是慢了一些。”
在他身邊,那些做應用研究,能拿橫向課題的同事們,課題經費和生活水平都有了顯著提升;但一直堅持基礎研究的他,仍然常常面臨資金不足的困境。去年發表的那篇《自然—通訊》論文,還是合作單位主動幫忙出的版面費。
侯書國也曾期待過,發篇好文章,或許能盡快評上職稱,還能從學校獲得一些經濟獎勵。但在目前破五唯的大環境下,他對這些的渴望沒那么強烈了。
或許,這篇《自然》論文帶給他的最大收獲,是終于得到了認可。“一名教輔系列的普通老師,也能實現自己的科研夢。”侯書國說。
“任何時候,都不要放棄夢想”
在今天的山東建筑大學,肉眼可見,年輕教師的“質量”在水漲船高。清華、北大的畢業生早不鮮見,海歸留學生的數量甚至更多。
“這一代的年輕學者,大多已經有了非常開闊的國際視野。就我所看到的,絕大多數碩士、博士,剛剛畢業時,都是躊躇滿志,想要大干一場。”侯書國說。
然而,有機會加入國內外一流研究平臺的年輕人,在任何時候都是少數。他們中的大部分人,在享受過優越的科研條件后,還是會落腳在地方的普通院校。等待他們的,難免有理念上的碰撞,與體制和氛圍的磨合,甚至失落、迷茫和孤獨。
該給這些年輕人什么建議呢?
第一次接受采訪時,侯書國并沒有想太清楚,只強調了一點:在找工作時,要好好考察,自己的研究方向與學校的主要發展方向是否吻合——這決定了未來很多年里,是事半功倍還是事倍功半。
次日,他又發來微信:“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深入地討論一下這個問題。”“我看到很多年輕人,來到地方院校遇到困難后,最終都選擇了‘入鄉隨俗’。但我想,還是應該保持一顆不甘平凡的心。”
他曾經和清華大學教授柴繼杰課題組合作,后者是施一公院士常常盛贊的得意弟子。柴繼杰本科學的是造紙專業,在造紙廠工作4年后,轉而讀研讀博,其間克服了種種困難。他剛到普林斯頓大學做博士后時,還是個“基礎差,英語也不行”的年輕人,如今已經成長為一名國際知名的結構生物學家了。
這個真正意義上的“逆襲”故事,也時時激勵著侯書國。
問題歸結為一個:如何在不夠理想的科研環境下,繼續堅持科研理想?他思考良久,總結出三個要點:
一是保持科研活力。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堅持跟蹤學科前沿,加強學術交流合作,定期參加本領域國內外高級別的學術會議。
二是盡可能保持一定的學術自由度。多數地方院校都會幫助年輕博士加入科研團隊,這些科研團隊的研究工作常常會和年輕人自己的研究方向存在偏差,進而束縛他們的研究自由。年輕人應盡量堅持兩條腿走路,一方面整合團隊研究,另一方面盡可能給自己留下一點獨立探索的空間。
三是腳踏實地,給自己規劃近期目標和遠期目標,按自己的節奏不斷為實現目標而努力。
孤獨過、失落過、后悔過、迷惘過,直到今天,或許也尚未達到真正的“不惑”,但某種意義上,侯書國仍然是個謹慎樂觀的理想主義者。
“不管什么時候,都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。”他說,“夢想是種什么樣的東西呢?大概就是——即便你不知道在夢想的引領下,能否走向預期中的成功;但你一定很清楚,沒有它,自己會變得何其平庸!”
相關論文:
https://doi.org/10.1038/s41586-022-04684-3
https://doi.org/10.1038/s41467-021-25580-w
https://doi.org/10.1371/journal.ppat.1004331
免責聲明:本網站所轉載的文字、圖片與視頻資料版權歸原創作者所有,如果涉及侵權,請第一時間聯系本網刪除。

官方微信
《腐蝕與防護網電子期刊》征訂啟事
- 投稿聯系:編輯部
- 電話:010-62316606-806
- 郵箱:fsfhzy666@163.com
- 腐蝕與防護網官方QQ群:140808414





